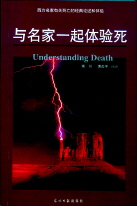在当代美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否认”人独特地遭遇到死亡的现实情况。对此观点,我们似乎半信半疑。这种观点通常引证的根据是习惯做法,如给尸体涂上香油,穿上盛装,进行整容。还有更为极端的做法,如关心棺柩密不透风、防止腐朽,却对许多临终病人的疾病漠然置之。
这些习惯做法普遍被作了如下解释:美国人正“趋于温和”,他们渐渐很少能够面对现实世界的严酷状况。在这种解释中,现实与严酷性时常是等同一致的,而生活中的令人愉快之事却被认为是不很“真实的”。人们说,美国人生活于一种虚幻的世界中,他们小心翼翼地防护着现实的入侵。我们对死亡的处理办法,可被看作一般可悲倾向中的惟一显著的证据。
本文将展示一种选择观。目前,美国社会已为一大批同行道的人设立了专门机构,尽管这些机构也变化多样,名称各异,但对死亡的倾向基本上不是持“否认”态度,而是采取了一种接受模式,此模式适合于我们行为主义的主要文化模式。我们要待评价了美国社会某些显著特点并讨论了死亡与垂死的某些方面之后,才能推进我们的论证。然而,似乎在此还应提出否定假设的一个基本难题:一个社会,若未完全将科学价值设立起来,以便采取一种与十分接近生物学和医学的科学现实主义截然相异的态度,那它就是不正常的。
死亡乃是一种自然现象,此现象源于人的以及所有高级有机体的生物学存在条件。加之,现代生物学确证,死亡不仅是高级有机体不可避免的,而且亦是在更为广泛的物理和有机系统中种类适应的一个积极的因素。
生殖质和体细胞之间的差异——此差异是高级生物体死亡率不同的关键所在——在适应方面看来,增加了遗传物质的稳定性和可变性。两性繁衍由于是将两个独立的遗传后代结合起来而产生新的、独一无二的遗传体质——此体质实际存在于后代的每一个体中,所以两性繁衍就有利于控制遗传变化。然而,倘若生物产生适应环境变化是为了积累更多的效能,那么亲代就必须死去,以使它的遗传物质能为新衍生的物质所替代。由此观之,死亡于生物学的适应来说实有一种积极的功效。
个体人格的死亡于此人格所从属的社会文化系统来说似乎有同样的功效。人类亲族系统倾向于规定社会文化体系和社会化过程中繁衍及其相互关系,虽然在这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独立的相互“作用”。亲族系统通过自己选择婚姻和维系家庭关系,既确定了社会中有机的社会的组成部分被不断结合起来的情况,又确定了如何使待合成的新生代服从于原初的认识过程,即将他们介绍给发展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在经由生命周期的成熟过程中,新生代最终将父辈遗传下来的社会文化模式内在化了。这样看来,较老的一代“行将消亡”,以便其后代能够“接替”社会的控制地位,尤其是接替老一代的繁衍和社会化的控制地位,后代也能够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自由地创新。遗传给特殊后代的文化模式同遗传模式一样是同生殖和父代呈现的亲族系统中的特殊的血统家系一道发生变化的。显而易见,死亡在文化模式的起源和变体利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还有适应社会的意义。
如此观之,不仅是作为科学家的我们,而且是所有变化的社会群体中的人类成员,都须将死亡认作人类状况的一个基本状况。凡人所活寿命正常适度,他就必须承受至少痛失某些与他亲近之人的重压。依靠存在着的人类及其定向行为,也依靠他们长期积累的复杂的符号体系,且也必须对此加以沉思。加之,死亡性必须并且始终是具体人类有限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证和清晰的象征。它是全能的障碍和能力的限度,它决不可能为人克服,而只能被人调整,被人接受。
现代社会中的达到老年人阶层的数字直线上升。美国人口现有9%都在65岁以上,相对来说,60岁以前却仅仅有4%。按我们社会的一般评论标准来看,这些人中的部分都已完成他们更为明显也更为重要的生命职责。一般看来,他们已经退职,孩子也长大成人,独立自主,有家有室了。按照他们社会地位的性质,他们也行将过世,并生活于“死亡的阴影”之中。他们正在进入——照大部分设定的标准来看——其生命的终了时期。这样,一个相对较大的团体就被组建起来,以便能够更为直接地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问题。况且,这种情形又影响了与老年人,尤其是与孩子密切相关的许多更为广泛的组织。因为这些孩子们必须对在相对不久的未来失去他们的父母有充分的精神准备。